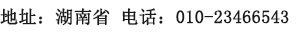浅析张怀瓘《文字论》中的书法理论思想
■齐明凯
张怀瓘,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唐朝书法家、书学理论家,代表作有《书断》《书议》《书估》《六体书论》《玉堂禁经》《文字论》等。其中,《文字论》是张怀瓘的一篇非常重要的书论,涉及很多有价值的议题。
一、对书法的再认识
对书法本质的认识,前人多从自然、心性、功用等多个维度去理解。如东汉蔡邕有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蔡邕肯定了书法的抒情性质,并谈到书者的创作心态。唐太宗曾说:“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这是从书法学习的角度切入的,认为书法是小学问,初学时不能急于求成。如果能够时时留心,胜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张怀瓘对文字和书法提出自己的看法:
文字者总而为言,若分而为义,则文者祖父,字者子孙。察其物形,得其文理,故谓之曰“文”。母子相生,孳乳浸多,因名之为“字”。题于竹帛,则目之曰“书”……其后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这句话不仅指出了文字的起源,还揭示了“文”和“字”的区别。张怀瓘在许慎观点的基础上有所增益,对“文”“字”“书”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番梳理后,接着便下一转语,谓书法乃是“翰墨之道”,是在“书”的基础上“加之以玄妙”所形成的,这句话言简意赅,却切中肯綮。
文字的发明、使用并不是出于审美的需要,历史上很多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字,但只有中国的文字超乎实用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张怀瓘对此认识很明确,他认为,要使“书”具有审美意义,必须“加之以玄妙”,这种“玄妙”是什么,张怀瓘没有进行具体说明。结合张怀瓘的其他书论著作如《玉堂禁经》《论用笔十法》《书诀》等,可知所谓“玄妙”表现在用笔、结构、章法、墨法等造型因素上,这就在理论上对书法的性质进行了肯定。
以“玄妙论”为基础,张怀瓘又提出“学书论”和“鉴赏论”。作为一门技艺,要想达到神乎其神的地步,必须勤学苦练。如虞世南所说:“自古贤哲,勤乎学而立其名,若不学,即没世而无闻矣。”虞世南认为,只有肯下苦功才能把书法练好。张怀瓘说:“虽功用多而有声,终性情少而无象。同乎糟粕,其味可知。不由灵台,必乏神气。”张怀瓘认为,书法没有“性情”就会味同嚼蜡,毫无趣味可言。因此,这就要求书家在勤学苦练的基础上,还要充分地发挥书家的“灵台”。
对于鉴赏者而言,除了欣赏书法的笔墨语言之外,还要充分地欣赏书作之外的意趣。张怀瓘多次强调“神采”,这比那些把书法比作具体事物的机械反映论者,要高明得多。从根本上说,书法是从天地万物抽象而来,定型之后,成为人们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所以,对于鉴赏者而言,要准确体会到其中的“神采”。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张怀瓘的审美鉴赏方法极为重视理性的作用。《文字论》中又说识书“若精意玄鉴,则物无遗照,何有不通”。可见,这种方法尽管不是具体的认知、理解、分析,但也不是纯由神行的直觉观照。
二、书法的实用功能
近代以来,说到书法,往往是指它的抒情、审美功能,有夸大其词之嫌。陈振濂在《中国现代书法史》中讲道:“首先是立足于书法作为艺术的观念立场,对过去实用加欣赏的混合机制进行认真有效的清理,强化它作为视觉艺术的应有特征而逐渐淡化它原有的作为实用工具的历史特征。”当代书法的价值与古代书法的价值差异较大,在古代,抒情、审美并不是书法的惟一价值、功能,除此还有诸如交流、政教、教育等非审美的功能。
张怀瓘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在《文字论》中叙述:
名言诸无,宰制群有。何幽不贯,何远不经?可谓事简而应博。范围宇宙,分别川原高下之可居,土壤沃瘠之可殖,是以八荒籍焉。纪纲人伦,显明政体。君父尊严,而爱敬尽礼;长幼班列,而上下有序,是以大道行焉。阐《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者,莫近乎书。
书法在古代的地位并不是主流,孙过庭在《书谱》中记录:“君子立身,务修其本,扬雄谓诗赋小道,壮夫所不为;况复溺思毫厘,沦精翰墨者也。”扬雄认为诗赋乃“小道”,胸有壮志的人不会只搞这一行。何况思维专注于用笔,精力沉溺到书法中呢?与扬雄持同样观点的人不少。张怀瓘的认识更加独特全面,提到书法既可以确定名分,使万事万物各得其所,也可以让伦理关系更加有秩序,使得社会更加和谐。可以看出,张怀瓘对书法的实用功能赋予了极大的神圣意义。书法不再是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甚至有阐发《五典》《三坟》的治国大道、成就国家盛大事业的功能,作用没有接近于书写的。
有好事者诘问:一味追求书法的实用性,会不会损害书法的审美性?这种问法太抽象,一方面把人当作抽象的个人,将人的各种社会关系一一剥离,另一方面受制于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将书法的各个功能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因而这种问法并没有多大意义。
三、“意象”观
“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易传》。《易传·系辞传》:“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句话是说圣人的想法可以通过典型的事情、形象表现出来。这种思路对后世文艺思想的影响很大。到了魏晋南北朝,刘勰就在此基础上提出“意象”的美学概念。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刘勰意为意在笔先,在下笔之前,想法就已明确,外物形象和艺术家的想法是紧密结合的。
“意象”是张怀瓘重要的审美准则。《文字论》中写道:“或若擒虎豹,有强梁拏攫之形;执蛟螭,见蚴蟉盘旋之势。探彼意象,如此规模,忽若电飞,或疑星坠。”由此可见,张怀瓘十分注重“意象”。叶朗说:“意象是美的本体,意象也是艺术的本体。中国传统美学给予‘意象’的最一般的规定,是‘情景交融’。中国传统美学认为,‘情’‘景’的统一乃是审美意象的基本结构。”“象”“意”两者是统一的,所谓“虎豹”“蛟螭”,不仅仅是对外在事物的描摹,更是书家主体情感的投射。
“意象”被张怀瓘视为一种批评标准。在众多书法家中,张怀瓘更为推崇张有道。张有道即东汉草书家张芝,不独张怀瓘一人,王羲之对他也是推崇备至。王羲之推崇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张怀瓘也评价张芝书法“精熟绝伦”,更是提到“意象”,即“惟张有道创意物象”“其书势不断绝,上下钩连”云云,这正是“意象”观在批评领域里的具体显现。
“意象”也是张怀瓘学书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表现为“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虽迹在尘壤,而志出云霄”。“元精”“神情润色”“志出云霄”都在用一种不能物化的语言表达书法的意象。今人学书法,择几种范本,矻矻临摹,更崇尚技法,离“元精”相去甚远。这跟近代科学的兴起有关系,另一方面,学书环境、方法、功用已然大不相同。
四、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很多论著提到张怀瓘书论中的道家思想,其实儒家思想对张怀瓘的书论影响也不容忽视。
张怀瓘《文字论》开篇讲文字的起源、功能,即“察其物形,得其文理,故谓之曰‘文’”,张怀瓘对文字功能的认识即与儒家思想关系较大。《论语》中有一个著名公案。子路问正“名”的意义,遭到了孔老夫子的批评。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李泽厚对此解说:“这大概就是儒家的语言学,极为重视语言的实用意义和实用价值,指出它在支配人的行为活动上的重要作用。其所以如此,‘名’(能指,书面语言)来自符号(指事),表示的是一种秩序、规范、法则,这就是‘实’(所指)。”可以理解为“名”起到规范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正因为有了“名”,万事万物才井然有序。张怀瓘重视文字的实用功能,即是儒家思想重视“名”的具体体现。
李泽厚指出:“《周易》这种认为自然与人事只有在运动变化中存在的看法,即‘生成’的基本观点,也正是中国美学高度重视运动、力量、韵律的世界观基础。整个天地宇宙既然存在于它们的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中,美和艺术也必须如此。”简单来说,儒家的美学思想更加重视气势、运动、力量。这在张怀瓘《文字论》中也有具体体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气势”,即“气势生乎流便,精魄出于锋芒”;二是审美趣尚更偏重于气势雄强的阳刚之美,诸如“虎豹”“蛟螭”之类均是凶猛狠鸷的动物。这都深受儒家美学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往往讲究以小见大、内在超越,比如盆栽“栽来小树连盆活,缩得群峰入座青”。书法更是如此,一个字即是一个自足的宇宙、一个完备的世界。《文字论》里提到“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这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这种哲学思想。
五、余论
书法创作和理论之间有紧密的联系,有书法创作能力的理论家更能切中肯綮。张怀瓘精通书法各体,自评“真行可比虞、褚,草欲独步于数百年间”,虽有夸大之嫌,但也正说明了张怀瓘有着扎实的书写功底,他的书法理论即使不作为指导书法创作的具体方法,却也有很强的操作性,正是这一点使得张怀瓘的书论更加缜密细致。总之,《文字论》篇幅虽短,但是它扼要地概括了张怀瓘书论思想的大部分内容。可以说,它具有一定的提纲性质。读懂《文字论》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张怀瓘的书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