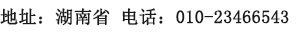西汉是中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奠定规模的时期,纵观整个西汉时期的礼制建设,我们以为呈现岀一定的阶段性,我们分为三期:
第一期,高、惠、文、景时期(含吕后专权时期)。这时期的礼制,基本沿用秦之旧制,祭天方面,在沿用秦代雍四畤的基础上,增设北畤,形成雍五畤的制度。汉髙祖不仅沿用秦旧仪,甚至祝官等也沿用秦,社稷也沿用秦代旧坛。宗庙方面,西汉前期也沿用秦始皇立生祠的作法(秦始皇作信宫于渭南,后改始皇极庙),太上皇庙、高庙和惠帝庙至迟在太上皇、高祖和惠帝驾崩的同年即已确立,文帝和景帝均自立生祠,死后由嗣位的皇帝改为帝庙,帝庙皆异地而处,不序昭穆。此外,惠帝时尊高庙为太祖庙,景帝时尊文帝庙为太宗庙,确立了西汉宗庙中不行迭毁的太祖、太宗之庙。
第二期,武、昭、宣时期。自汉武帝开始,一方面遵循秦代的礼仪旧制,一方面致力于确立西汉王朝自己的礼仪制度。在继续沿用郊雍的祭天传统的同时,汉武帝在甘泉设泰畤,在汾阴设后土祠,文帝时又曾在长安附近设立五帝庙和五帝坛,开始摆脱秦人祭天传统的束缚。宗庙制度方面,宣帝时尊武帝庙为世宗庙,使西汉宗庙中不行迭毁的一祖二宗之庙得以完善。此外,宣帝时还立五星祠于长安城旁,阴阳五行观念开始影响都城礼制建筑的分布。
第三期,元、成、哀、平、新葬时期。这一时期的礼制改革虽然历经反复,却最终奠定了以后历代都城礼制建筑的规划原则,元帝时,开始实行宗庙迭毁的制度。从汉成帝开始,直至新葬时期,在匡衡、王莽等人的主持下,《周礼》所规定的祭天地于都城南北郊和“兆五帝于四郊”的制度正式付诸实施。祭天享祖的明堂、作为教化之所的辟雍、望观云物的灵台以及讲经习礼释奠先师的太学等礼制建筑也得以确立。这些礼制改革的措施,对以后历代都城礼制建筑的设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明堂、辟雍、灵台、太学是否分立的问题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西汉末期修建的礼制设施中,至少灵台、太学是单独设立的.明堂与辟雍是合为一体还是各自分立的,目前尚南确断,从文献记载金石著录的情况来看,有相当多的信息表明当时明堂与牌雍可能是分立的;
杨谁《剧秦美新文》称:“明堂、棄台,壮观也;九庙、长寿,极寿也”(按文辞对仗的原则,明堂与雍台(辟雍与灵台)是并列的成分,九庙与长寿(王莽为元帝皇后王氏修建的长寿宫,后攻新室文母庙)也是并列的成分,都是指建筑物的名称)。此外,清代徐松考订唐长安城里坊,也认为明堂、辟雍是分立的。我们现在不能确知徐松之所据,所以暂不作为立论的依据。
东汉光武帝时期在雜阳设立了明堂、辟雍、灵台和太学,这些礼制建筑的修建,是参考了西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而且光武帝自己也曾亲临西京,当时西京南郊的礼制建筑虽然已经被焚毁,但遗迹尚存,基阙犹在,他应该是看到过的。西京南郊礼制建筑是在新莽地皇四年(23年)焚毁的,东汉锥阳城南郊明堂辟命的修建时间是在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56年),上距西京明堂辟雍焚毁的时间不过33年。考古发掘的結果证实,东汉锥阳城南郊的明堂、辟雍就是分立的,这也可以看作西汉长安城南郊明堂、辟雍二者分立的—个佐证。
我们注意到,“王莽九庙”遗址的第12号址位于1-11号建筑遗址大围壻之外,自成一体。该遗址的中心建筑,较之1-11号的中心建筑要大一倍,其内部建筑结构,同1-11号址也有不同12号址也作五室,其建筑结构与“明堂辟雅”遗址大体一致。这正与文献记载中明堂与辟雍建筑结构基本相同,只是一圜水,一不圜水的情况相符合。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不妨提出以下设想:西汉长安城南郊的明堂、辟雍、灵台、太学是各自分立的,所谓的“明堂辟雍”遗址为辟雍遗址,“王莽九庙”的第12号址为明堂遗址。这个设想,当然还需要留待“王莽九庙”遗址发掘报告面世以后再作检讨,更需要得到以后考古发掘工作的验证。
西汉礼制改革的两个趋势
西汉长安城礼制建筑的设置与变更,存在着两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阴阳五行学说逐步成为指导都城礼制建筑布置的指导性原则,都城的郊祀制度日趋完备。汉髙祖时,在秦代祭四帝的基础上,增加黑帝,使祭天五帝的制度趋于完善;汉宣帝时,立五星祠于长安城旁;西汉末年,则开始放弃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及雍五畤的祭祀,按照阴阳五行的观念,改在长安城南北郊祭祀天地,以就阴阳;“兆五帝于四郊”,按照五行的方位设置蔡坛。从而确立了阴阳五行观念在规划都城礼制建筑方面的指导地位。
第二个趋势是,繁复的祭祀活动被删繁就简,有逐步规范、简化的改革倾向。比如宗庙方面,元成之时,针对京师郡国遍布庙宇的情况,韦玄成、匡衡等就提出“庙宜一居京师,夭子亲奉,郡国庙可止毋修”的建议。他们还提出宗庙迭毁的建议也针对雍五畤祭祀繁复的情况,匡衡曾提岀罢除雍五畤的建议,一度为汉成帝所釆纳成.汉成帝末年颇好鬼神,听信奸人之说,广设神祠于长安,费用甚多。大臣谷永以《论语》中“子不语怪神”来奉劝成帝,“唯陛下距绝此类,毋令奸人以窥朝者”,受到汉成帝的赞许。
西汉末年简化祭祀礼仪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减省祭祀对象。成帝时,匡衡提议罢除雍五畤及陈宝祠。后匡街又奏议废止不合礼仪的祠庙四百七十五所。成帝末年,谷永劝成帝减省长安城旁诸杂祠。平帝时,王葬奏毋修渭阳祠。这些奏议,大多被当朝皇帝釆纳(但也有反复,这正是礼制改革所不可避免的)。
2、将远离长安的祠庙迁至长安附近,去行礼时舟车劳顿之苦。文帝时立五帝坛、五帝祠于长安城郊,实际上是对雍地五帝畤的迁移。宣帝时,立五星祠于长安,也是意欲迁雍地五星祠于长安。西汉末年迁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于长安南北郊,目的之一就在于减省行事时的劳顿之苦。
3、将群神以类相从,避免重复祭祀,王莽时按照调礼》“兆五帝于四郊”的说法,“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祭祀于长安四郊。
事实上,按照阴阳五行的观念规范、简化祭祀制度是贯穿整个中国封建时期的。关于这—点,在下文的分析中,还可得到进一步的论证。此外,后世颇受重视的一些礼制项目,在西汉时期虽然没有形成制度,但已出现萌芽,如朝日夕月、耕籍亲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