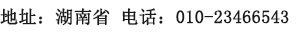春天悄没声息地给大地万物染上了美丽的绿色,看着窗外明丽的春天暖阳,很想出去掐一回苜蓿。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苜蓿原处大宛,汉使张骞带回中国,然今处处田野见之"。唐诗中有:"降纱谅无有,苜蓿聊可食",每到春天吃苜蓿之心急不可待,恰好一同事说学校背后,凤口高速路出口处的苜蓿很茂盛,放学后便欣然相约前去。
没想到比我们早来大姐大嫂们已经蹲了一地,远处看去就像绿色的缎面上缝制了五颜六色的一朵朵大小彩色蘑菇,现代人生活好,穿戴时髦,农村人比城里人穿的还时尚高档,再走近一阵阵欢声笑语迎面扑来,这里是陕甘交界处,来这里掐苜蓿的大多是留守农村的中老年妇女,热情不怯生的的大嫂的招呼声也迎面送上,一时间温馨的暖意和放松的心情在心里油然而生,感觉他们过着无拘无束的好生活,不像我们整天钻在办公室里,缺失了良好的空气,养成了古板的性格。女人们拉着各自的家常,谁家男人外出打工昨天回家了,拿回了多少人民币,谁家闺女大学毕业在城里找到了好工作,工资每月六七千,把父母接城里去了,不时说着笑话,互相打趣,以前不认识的人都好像认识了多年的老朋友,但手里却没停下掐苜蓿的活,一时间篮子就满了,连我手里的大塑料袋也满了,大家吆喝着笑侃着,互相夸赞看谁的手快掐得多,不知谁提议,该回家了,我才意识到,天已经快黑了。
看着这一袋子绿色,我就不由自主的想:缺吃少穿的岁月如果能蒸上几碗菜疙瘩,或者蒸上一笼菜坨坨,或者开水里烫过,凉拌两碟子苜蓿菜,一家人聚在一起,准是一顿美味佳肴!"过去人可怜的,吃苜蓿也没有",走在前边的大嫂和我的心遥相呼应,也开始忆苦思甜了。是的,现代人吃苜蓿多是想换换口味和追求绿色环保的理念,可生在六十年代的人就不是了,每到春季是日子最难熬的时候,粮食已经青黄不接,春季二三月的天又特别长,生产队里分的粮食早吃完了,春季多亏野菜救急,那时候苜蓿是生产队公有的,为了免受饥饿,大人娃娃几乎都有偷苜蓿的历史。
我小时家里十四口人,只有叔父婶婶妈妈挣工分维持生计,妈妈和婶婶还有叔父,老是半夜里在田涧地头偷苜蓿,母亲和婶婶一次被看苜蓿的人都追到悬崖边上,母亲回家时一只鞋子都跑丢了,还险些丢了性命。还有一次家里当天就断顿了,叔父在灵台偷偷的买"黑市"玉米,被市管会人员追赶,叔父上着坡还背着粮食,被追撵玉米撒了一地,回来的看见的只是不足十斤的玉米和石头沙子的混装,但却在灵台半山上收获了一大口袋苜蓿,为全家那天的生活救了急。那时的小孩子很懂事,早早知道为父母分忧,我们姐妹兄弟八个,六个女孩为大,但最大的我也只有十多岁,出去拾野菜,拾麦子,拾柴禾,大的带着小的老是是满满一大筐,掐苜蓿偷苜蓿是我们姐妹最拿手的本领,看谁手快,每个人都会满载而归,回来能看到大人赞许的目光就很满足,看见大人凄苦的眼神也全然不理会。
这期间我们姐妹多次遭遇人追狗撵,时不时看见过田间地头涧畔,由于饥饿和缺医少药而丧失的幼小的生命尸体,常常衣不裹体,红的绿的布头相随,看见了吓得一路小跑,也看见过野狼叼走过鲜活的生命,更看见过吃野菜中毒,面目肿大而不治身亡的人,有些人吃野菜脸色变成菜色,也不停听说这里那里饿死了人。但我那时毕竟是小孩子,一旦回到那个连锅都是破的,每顿做饭前要用面糊补的家,只要看见奶奶给我们做的苜蓿菜高粱饼子,苜蓿菜玉米面,苜蓿菜疙瘩汤,苜蓿菜麦饭就高兴得忘了一切,争着抢着填饱肚子,觉得什么时候不缺吃穿,那就是多么幸福和明媚的日子!
这些年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饭桌上鱼肉时鲜总是不断,下馆子吃一顿,点几道生猛海鲜,特色佳肴也是常有的事,尽管各种餐厅厨艺精湛,美味佳肴,色香味俱全,但吃来吃去,总比不上儿时饭桌上那奶奶亲手做碧绿清香的苜蓿味。儿时的记忆依稀可鉴,那时人们只是为填饱肚子,并不懂得健康食品这一概念。
想起已经逝去的童年,似乎闻到了苜蓿的清香,左邻右舍的孩子提着苜蓿篮子,追逐穿梭于田间地头,你追我赶,嬉戏玩闹,自有许多乐趣在其中。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似乎也看到了祖辈的身影和对生活的凝望。如今生活的安然舒适,生活水平一天天提升,但我们更应记住我们曾经的苦涩,才能更好去体味今天的幸福。这就是我的那一份对苜蓿无法释然的情结和怀念,一抹关于春天的清香苦涩的记忆。
作者简介:
武秋萍,大学文化,一级教师,从教38年,喜欢阅读写作,旅游摄影,音乐舞蹈,英语口语等。
大家都在看长武桃花朵朵开,美得辣眼睛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王小艳热烈祝贺一纸馋纸包鱼(长武店)15号正式试营业啦~黄土塬走出的作家——郝贵平有一处美景叫天蓝蓝:五月就来看浅水塬投稿/合作(注明来意)
赞赏